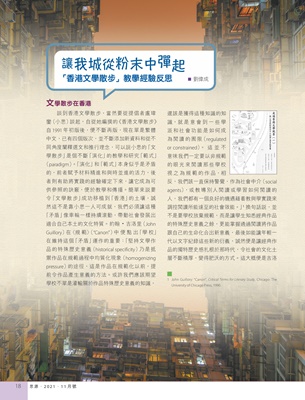
思源.2021. 11月號
18
讓我城從粉末中彈起
「香港文學散步」教學經驗反思 劉偉成
文學散步在香港
談到香港文學散步,當然要從提倡者盧瑋
鑾(小思)談起,自從她編撰的《香港文學散步》
自1991 年初版後,便不斷再版,現在單是繁體
中文,已有四個版次,並不斷添加新資料和從不
同角度闡釋選文和推行理念,可以說小思的「文
學散步」是個不斷「演化」的教學和研究「範式」
(paradigm)。「演化」和「範式」本身似乎是矛盾
的,前者賦予材料精進和與時並進的活力,後
者則有助將實踐的經驗確定下來,讓它成為可
供參照的訣竅,便於教學和傳播。簡單來說要
令「文學散步」成功移植到「香港」的土壤,誠
然這不是靠小思一人可成就,我們必須讓這種
「矛盾」像車輪一樣持續滾動,帶動社會發展出
適合自己本土的文化特質。約翰 ‧ 吉洛里(John
Guillory)在〈 規 範 〉( "Canon")中便點出「學校」
在維持這個「矛盾」運作的重要:「堅持文學作
品的特殊歷史意義(historical specificity)乃是抵
禦作品在規範過程中均質化現象(homogenizing
pressure)的途徑,這是作品在規範化以前,提
前令作品產生意義的方法。或許我們應該期望
學校不單是灌輸關於作品特殊歷史意義的知識,
還該是獲得這種知識的知
識,就是意會到一些學
派和社會功能是如何成
為閱讀的囿限(regulated
or constrained)。這並不
意味我們一定要以非規範
的眼光來閱讀那些學校
視之為規範的作品,相
反,我們該一直保持警覺,作為社會中介(social
agents),或教導別人閱讀或學習如何閱讀的
人,我們都有一個良好的機遇藉着教與學實踐來
調控閱讀所能達至的社會效能。」1 換句話說,並
不是要學校放棄規範,而是讓學生知悉經典作品
的特殊歷史意義之餘,更能掌握通過閱讀將作品
跟自己的生命化合出新意義,最後如能讓年輕一
代以文字紀錄這些新的衍義,誠然便是讓經典作
品的獨特歷史感扎根於那時代,令社會的文化土
層不斷積厚,變得肥沃的方式。這大概便是吉洛
1 John Guillory: "Canon", Critical Terms for Literary Study, Chicago: The
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, 1990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