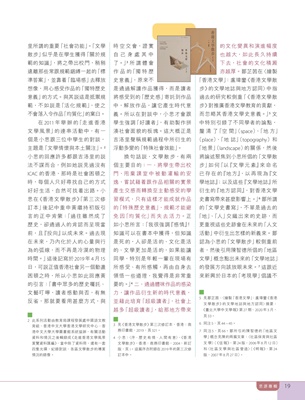
19
思源專輯
里所謂的重要「社會功能」。「文學
散步」似乎是在學生獲得「關於規
範的知識」,將之帶出校門,稍稍
遠離那些常跟規範綑縛一起的「標
準答案」,並靠着「臨場感」去釋放
想像,用心感受作品的「獨特歷史
意義」的方式。與其說這是抵禦規
範,不如說是「活化規範」,使之
不會落入令作品「均質化」的窠臼。
在2011年舉辦的「走進香港
文學風景」的連串活動中,有一
個是小思跟三位中學生的對談,
主題是「文學情懷與本土關注」。2
小思的回應許多都跟吉洛里的說
法不謀而合,例如她說見過沒有
ICAC 的香港,那時是社會困頓之
時,每個人只好尋找自己的方式
好好生活,自然可找着出路。小
思在《香港文學散步》「第三次修
訂本」後記中重申黃繼持初版引
言的正中肯綮:「過往雖然成了
歷史,卻通過人的肯認而呈現當
前,且『投向』以成未來。過去現
在未來,乃內化於人的心量與行
為的弧線,而不再是冷漠的物理
時間。」這後記寫於2019年4月15
日,可說正值香港社會另一個動盪
困頓之時,所以小思如此回應黃
的引言:「書中眾多的歷史囑託、
文藝叮嚀,讀者感動與否,有無
反省,那就要看用甚麼方式,與
2 此系列活動由教育局課程發展處中國語文教
育組、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文學研究中心、香
港中文大學大學圖書館系統協辦,有關活動
資料和情況之後輯錄成《走進香港文學風景
賞覽資料匯編》,當中除了資料冊,還有一套
四隻光碟,紀錄對談、各區文學散步的導賞
情況的錄像。
的文化變異和演進幅度
也越大,如此長久持續
下去,社會的文化積澱
亦越厚。鄒芷茵在〈繪製
「香港文學」:盧瑋鑾《香港文學散
步》的文學地誌與地方認同〉中指
過去的研究較側重「《香港文學散
步》對推廣香港文學教育的貢獻,
而忽略其香港文學史意義。」5 文
中特別引錄了不同學者的論點,
釐清了「空間」(space)、「 地 方 」
(place)、「 地 誌 」( topography)和
「地景」(landscape)的關係,然後
將論述聚焦到小思所倡的「文學散
步」如何「以『文學元素』來命名
已存在的『地方』,以再現為『文
學地誌』;以及這些『文學地誌』所
衍生的『地方認同』,對香港文學
史書寫帶來甚麼影響上。」6 鄒所謂
的「文學史書寫」,不單是過去的
「地」、「人」交織出來的史跡,而
更重視這些史跡會在未來的「人文
活動」中衍生出怎樣的新義來。鄒
認為小思的「文學散步」較側重前
者,然後引用陳智德所倡的「地區
文學」概念點出未來的「文學地誌」
的發展方向該放眼未來。7 這跟近
來新興於日本的「考現學」倡議不
5 見鄒芷茵:〈繪製「香港文學」:盧瑋鑾《香港
文學散步》的文學地誌與地方認同〉摘要:
《臺北大學中文學報》第27期,2020年3月,
頁33。
6 同注5,頁44-45。
7 同注5,頁66。鄒所引的陳智德的「地區文
學」概念見陳的兩篇文章:〈社區保育與社區
文 學〉(《信 報》,第 24版,2006年8月12日)
和〈社區文學與社區營造〉(《明報》,第24
版,2007年8月27日 )。
時空交會,證實
自己身處其中
了。」3 所謂體會
作品的「獨特歷
史意義」,原來不
是通過解讀作品獲得,而是讀者
將感受到的「歷史感」寄託到作品
中,解放作品,讓它產生時代意
義。所以在對談中,小思才會跟
學生強調「好讀者」,有助製作拼
湊社會面貌的板塊。這大概正是
吉洛里聲稱規範過程中所衍生的
浮動多變的「特殊社會效能」。
換句話說,文學散步,有兩
個主要目的:一、將學生帶出校
門,甩棄課室中被動灌輸的安
逸,嘗試藉着跟作品相關的實景
產生交感而轉換至主動感受的學
習模式,只有這樣才能成就作品
的「特殊歷史意義」,規範才能避
免因「均質化」而失去活力。正
如小思所言:「我很強調『感情』!
知識可以在書本中獲得,但知識
是死的,人卻是活的、文化是活
的、文學更加是活的,如果能讓
同學,特別是年輕一輩在現場有
所感受、有所感觸,再由自身去
領悟一些道理,我覺得是非常重
要的。」4 二、通過體味作品的感染
力,讓作品衍生新的時代意義,
並藉此培育「超級讀者」,社會上
越多「超級讀者」,給那地方帶來
3 見《香港文學散步》第三次修訂本,香港:商
務印書館,2019,頁321。
4 小 思:〈序・歷史有情、人間有意〉,《香港
文學散步》,香港:商務印書館,2004,新訂
版,頁 i。這篇序亦附錄在2019年的第三次修
訂本中。